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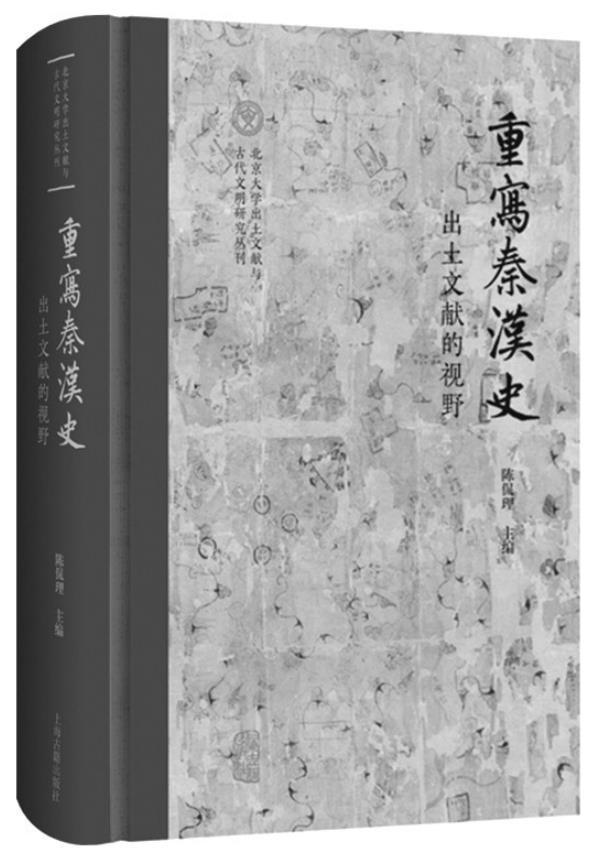
孟育芬
看点
20世纪初以来,秦汉简帛及其他出土文献资料大量涌现,源源不断地为秦汉历史文化研究提供新材料,《重写秦汉史:出土文献的视野》就是在出土文献的视野下探讨如何“重写秦汉史”。本书旨在扭转秦汉史研究的碎片化趋势,为未来的研究确立更高的起点,提供更广阔的视野,同时也反思其得失,让人们了解出土文献与秦汉史研究的现状和所取得的成果,融会以启新。
中国古代史学以“前四史”为经典,而秦汉史独占其三。司马迁、班固、范晔用他们的如椽巨笔描绘了波澜壮阔的世变、瑰奇多姿的人物,让人心驰神往,读之忘倦。直到20世纪初,秦汉史研究几乎相当于研读《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史”塑造了后人对秦汉史的认知,也让人们形成了对2000年封建社会的诸多基本印象。
新一代秦汉史研究者,在成长过程中不断受惠于出土文献,他们不断总结秦汉史研究在出土文献的视野下所取得的推进。为此,10年前,一群青年研究者相约,每人选择一个自己比较熟悉或正在探索的重要领域,介绍相关的出土资料、研究课题、最新进展和自己的心得,编成一书,这就是《重写秦汉史:出土文献的视野》(以下简称《重写秦汉史》)一书的由来。
《重写秦汉史》全书分为文字发展、文书行政、律令法系、徭役制度、军事制度、政区地理、信仰世界、时间秩序、里耶秦简九章,由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北京大学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所研究员陈侃理主编,并由9位具有代表性的新锐学者分别撰写,着力梳理各专业领域的主要出土文献和研究进展,阐发作者的最新研究见解,揭示学界利用出土文献资料已经取得的新认识。
陈侃理介绍,从2013年开始酝酿写作这本书时起,就期待它会将秦汉史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扭转秦汉史研究的碎片化趋势。从初稿到定稿,过程变得艰难,几乎每一章的文稿都反复修改,有的甚至改变原初的设想,推倒重来。在这个过程中,新资料和新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作者的想法也在持续更新,几位作者要一起按时完成定稿,困难可想而知。“五年计划”,倏忽间变成了“十年磨一剑”。回首十年,陈侃理在“后记”中写道:“出土文献自从被定为‘冷门绝学’,就免不了要‘过热’;而‘沉淀’下来,变得更紧要也更困难。这部书的编撰本身似乎也已经成为一个转变时期的见证,而有了特殊的意义——在这以前它不会产生,在这以后它也不会再以这样的方式产生。”
如今,秦汉史已经从钻研旧籍的古典学问,变为需要密切关注新发现、综合不同类型史料、利用多学科方法的新兴学术。新出版的秦汉史研究论著大部分与出土文献有关,甚至围绕出土文献展开。学者们对秦汉时代的认识不再限于史书所传达的,甚至在许多方面超过了史书的作者。因此,新一代的秦汉史研究者在《史记》《汉书》古书以外,还必须通晓出土文献,以此为基础打开视域。
为什么出土文献缺少不得?出土文献究竟为秦汉史研究提供了哪些以往没有的新知识?秦汉史研究中哪些基本问题是通过出土文献形成的?时下,出土文献已经进入了秦汉史的主流论述,新编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也用上了简牍资料。通过出土文献来研究秦汉史,需要丰厚的知识储备和学术积累,任何研究者都在不断学习之中。《重写秦汉史》从学界的总体观察,提出了有待改进工作的方面,比如提高资料整理水平,建立全面、可靠、公开的数据库;及时梳理学术史,更新研究课题,增强问题意识。
如果说文字是文明形成的标志之一,文字的发展、演变可以说是文明历史最直观的表现。今天仍在使用的汉字,大致是在秦汉时期定型的,而秦汉时期的文字又是古隶、八分、草书、行楷等多体并存,其丰富和复杂程度在历史上实属罕见。过去,存世的秦汉文字仅有金石铭刻,限制了人们对秦汉文字丰富性的认识。在《重写秦汉史》一书中,郭永秉撰写第一章《文字发展》,充分利用上世纪以来发现的各类型文字资料,精选石刻、铜器铭文、模印或刻画陶文、简帛古书和简牍文书等,展现出写刻工具、载体、方法、用途等不同因素导致的字体变异。他特别强调,文字书写追求速度和追求典丽的不同需求产生出所谓“正”“俗”之分,两者又分别孕育出了八分、楷书以及草书、行书等新书体。这提示我们在观察文字演变时,要将时间和场合两个维度结合起来考虑。一旦关注了出土文献中文字的“体”和“用”,作为文字使用者的人的活动就从中浮现出来。我们可以思考:书写者如何获得读写技能,如何通过书写获取政治、社会、文化资源,他们与所书写的文本和载体之间是什么关系,又用何种态度对待某个特定的书写行为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广阔的想象和探索空间。
东汉王充在《论衡》中说:“汉所以能制九州者,文书之力也。”秦汉国家能够在广大的地域中实现中央集权的官僚统治,依靠的技术手段正是文书行政。文书行政不仅指能够利用文书来行政,而且意味着正式的行政作为必须通过文书来实施和记录。在后一个意义上,它构成了秦汉有别于其他文明的重要特征。
简牍帛书新发现的消息一出,往往万众瞩目,翘首以待,但资料的整理工作本身却相当艰苦、枯燥而且难免疏失。《重写秦汉史》作者认为,有关秦汉史的出土文献研究,至少在三个方面值得加强。一是重视出土文献的“本体”研究,重视其作为文物的性质,在形态复原、文本释读和考证年代、性质等方面投入足够的关注,让这一步成为研究历史文化必须要有的前提,并且尽可能从出土文献材料自身的特性中提出新问题。二是要充分了解出土文献的特性和局限,认清它作为同时期史料,往往原始、直接,然而也未经概括、不成系统,往往失于片面或看似客观而实则经过选择和修饰。三是要强调综合研究,处理好新旧出土文献的关系、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关系,把握好宏观概括与微观细节的关系,使得彼此优势互补、合而双美。在上述三个方面,《重写秦汉史》一书的作者都作了努力,读者不难在各章中找到有关的例子。
历史上的研究对象好比业已消融的冰山,古人描画了它的轮廓,而出土文献则是偶然崩落到我们手中的碎片。这块碎片来自冰山本身,有着任何图像都描摹不出的温度、质感、味道。但冰山毕竟不是冰块,只有把碎片放到整座冰山的影像中去,才能充分认识两者,并获得一种想象的能力,去思考潜藏在海平面以下的巨大存在。
责编:姚晟琦
审核:徐晓敬
Copyright © 2024 lnd.com.cn 北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