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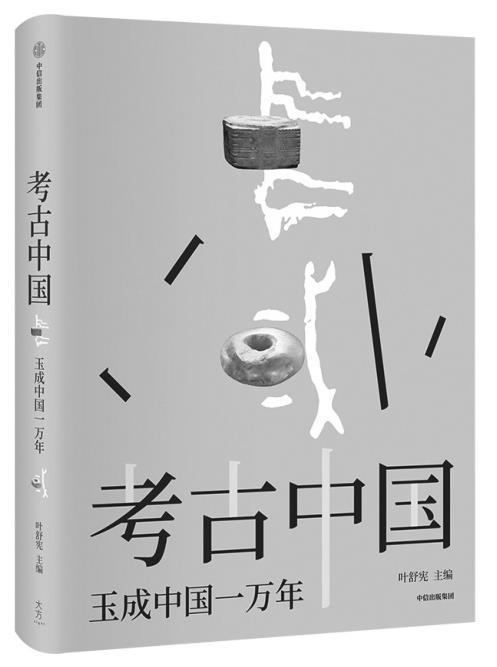
沈茂华
1793年,乔治·马戛尔尼率英国使团访问中国。在这场载入史册的著名会面中,清乾隆皇帝赠送给他的第一件礼物是玉如意,马戛尔尼后来回忆:“这是一个白色的、玛瑙般的石头,大约有一英尺半长,雕刻着奇怪的图案,中国人对它极为重视,但对我来说,它本身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价值。”
这并不只是英国人的傲慢,因为玉器在欧洲文化中确实没什么特殊的意义。欧洲人直到16世纪西班牙人征服阿兹特克帝国时,才第一次知晓玉(软玉)。即便如此,西班牙人把玉从美洲带回来时,也仅仅看作是佩戴在腰间、防止肾病的护身符,所以西班牙语称之为piedra de ijada(“治肾病的石头”),此后辗转经过法国文化引介,jade(翡翠、绿宝石)一词1721年才进入英语。可想而知,对当时的英国人来说,那不过是一种异域传入的装饰品罢了。
中国人对玉的喜爱已习以为常,以至于常常意识不到,放眼全世界,这种玉文化其实非常特别:古代世界只有三大玉作中心,另两个(中美洲印第安文明、新西兰毛利文化)还都是远离旧大陆文明的边缘地带,更从未像中国这样,玉作工艺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得到充分发展。考古学家苏秉琦曾将1万年以内的中国新石器文化划分为相对稳定的六大文化区系,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玉崇拜。国学大师季羡林曾这样概括:“如果用一种物质代表中华文化,那就是玉。”
问题就在这里:玉石再特殊,说到底也仍是石头,为什么中国人为这些石头赋予了如此高的文化价值?甚至还把这当作是一系列文化价值的核心?
当然,中国境内的玉矿资源储备确实极为丰富:东极以辽宁省岫岩玉和宽甸玉为代表,西极则有喀喇昆仑山脉的和田玉,从北到南,也都有玉石分布。现在的考古发现证实,北方玉矿原料的供应和传播,催生出了万年前的东北玉文化。正如《考古中国——玉成中国一万年》书中所言,“审视玉文化起源,如今的东北三省是当之无愧的始源地区”,中国“四大名玉”,岫岩玉更是最早被先民开发使用的,其初始时间早至距今2万年前。1982年,阜新查海遗址出土的玉器,表明早在8000年前,中国人就已掌握了高难度的攻玉技术,被誉为“世界第一玉”。
不过,玉石资源丰富,未必就催生出相应的玉文化——和田玉历代闻名,但那只是供应中原,本地文化对玉本身并无偏爱。良渚文化是神王之国,将玉视为权力、地位、财富的象征,各种玉器琳琅满目,然而它所在的江南水乡并不盛产玉石。也就是说,物质资源的丰富可能既非这种特殊文化取向的必要条件,更非充分条件。
一个社会之所以对某种物质赋予特殊价值,与其文化理念紧密相关,即便是作为“天然货币”的黄金,当年美洲印第安人也完全无法理解为何发现新大陆的白人会对这种金属如此疯狂寻求。需求才是关键:只要存在这种文化渴求,人们会不远万里去搜寻,东北岫岩、西北和田,都不是问题,反倒还更“物以稀为贵”。那么玉崇拜在中国文化中产生的原因到底何在?
神话学家米尔恰·伊利亚德曾表示,高山往往被早期文明视为神的居所,是“天空与大地相遇之处”,因而也是“中心点”,是充满神圣的地方。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文化中“升仙”的传说:许多人修仙都偏好深山,那不仅是因为远离世俗尘嚣,恐怕也因为那被视为接触神圣性的所在,而玉看上去像是高山的“精华”,那么谁佩戴、使用玉,当然也就是具有特殊力量且能与神灵沟通的非凡之人。
石头本身就是一种永恒的存在。麦加天房里的克尔白黑石为所有穆斯林共同崇拜,苏格兰历代国王都要在斯昆石上加冕,而那乍看起来似乎也只是一块平淡无奇的大石头。重要的不是这些物质存在如何贵重,而是对它的崇拜为群体提供了一种必要的凝聚力。在非洲的阿散蒂文明中,黄金王座是王权的象征,甚至比君主本身更优先,无论阿散蒂国家如何变动,它是所有人都承认、敬拜的恒常之物,全社会的秩序都奠基于黄金王座的神秘性之上。
玉比普通的巨石珍稀,小型的玉器也便于移动、佩戴,适合充当巫师的法器,当然也不用像提炼黄金那样需要高温冶炼技术(炼金术在古代可是高科技),虽然也要经过采矿、设计、切割、打磨、钻孔、雕刻、抛光等多道工序,但即便没有金属工具,也能制作出来。这样,对新石器时代的华夏先民来说,玉在功能上为社会凝聚、文明诞生提供了必要的支撑点,一个日渐的分化的复杂社会得以围绕着它构筑起新秩序。
汉字“国”就是这一理念的缩影:其繁体字“國”寓意以武器“戈”守卫城池内的邦国珍宝,简体的“国”是俗字,代表着四方城墙的中央供奉着最高价值之物——玉。收录9000多字的《说文解字》,在编排时将一、二、示、三、王、玉这六个部首排在字典的首要位置,那既不是因为笔画,当然更不是因为拼音,而是体现出一种神话宇宙观:对古人来说,“示”(神灵、祭祀)、“王”和“玉”是最为重要的存在,而神权和王权都是借助于玉器才得以成立。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像玉钺这样的器物是君主手握生杀大权的符号物,但玉器毕竟不像金属工具,这种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精神性的,没有那么强的暴力色彩,更注重的是守卫“礼”的社会秩序。换句话说,先秦的这些君主大多是集神权和王权于一身的“神王”,但神权先于王权,社会重于国家,国家作为一个垄断暴力的组织是从社群的母体中分娩出来的。
这一点,在这本《考古中国——玉成中国一万年》中斑斑可见,凡有玉器出土的全国各地先秦考古遗址,实际上都具备了城邦国家诞生的雏形。这些遗址的广泛分布,也意味着在新石器时代,随着玉崇拜的传播,中华大地上已经出现了“满天星”的态势,由此可以证明考古学家苏秉琦的判断,远不只是传统上认定的那样,是在黄河流域单一起源。不仅如此,这也可以证明“华夏五千年”和中国文化的内在统一性:“玉文化在距今5000年之际先统一长三角,其后又在距今4000年之际,大体上统一了中国。”
至此,中国文明的一个重要特质已得以奠定,社会学家费孝通用“玉魂国魄”来概括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堪称精到。不过,问题并未到此为止,仍有一系列问题有待我们思考:在原始的交通条件下,先秦时期遍布全国的玉文化及其工艺是如何传播的?这种既有统一性,又各具地方差异性的多元文化面貌意味着什么?如果说玉文化是原生的大传统,金属文化是次生的小传统,那么商代以青铜器为主的金属礼器是如何后来居上的?又为什么青铜器、金银器从未真正取代玉器的地位,直到今天中国人仍然那么喜欢玉器?当然,那可能就需要另一本书才能回答了。
编辑:王天琪
责编:闫尚
审核:徐晓敬
Copyright © 2024 lnd.com.cn 北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