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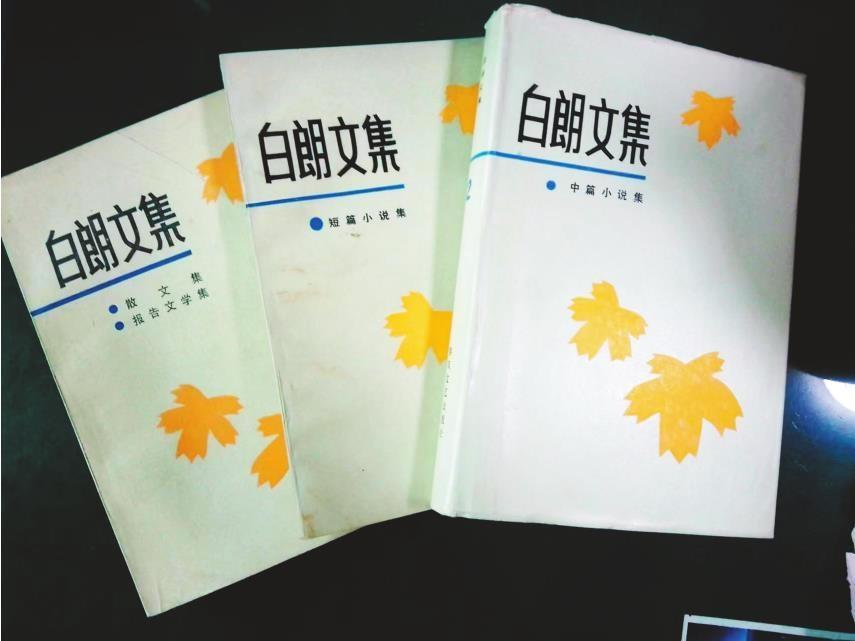
徐光荣珍藏的《白朗文集》。当年,他带着这套文集拜访了白朗和罗烽。
本报记者 刘臣君
核心提示
在20世纪中国文学版图中,写下短篇小说集《伊瓦鲁河畔》的白朗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她生于沈阳,出身中医世家,后成为东北作家群中与萧红齐名的女作家。她手中的笔兼具双重力量,既描摹民众的苦难,又成为反抗侵略者的武器。
自九一八事变后踏上创作之路,到跟随流亡队伍辗转南下,再到与萧红在抗日烽火中相互扶持,白朗的人生轨迹始终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
从辽河女儿到左翼尖兵
“我在写《辽宁省志·文学卷》时,写下了一段评论——1934年以后,流亡到关内的东北作家逐渐形成了‘东北作家群’,在这个作家群中,辽宁作家的创作占有重要地位。白朗,这一时期出版短篇小说集《伊瓦鲁河畔》。她是沈阳人,原名刘东兰。《伊瓦鲁河畔》收入7篇小说,歌颂了东北人民的反抗斗争,抒写了对关东沃土的眷恋。”《辽宁文学史》《辽宁文学概述》作者徐光荣说。
8月15日,由辽宁省作家协会和沈阳出版社联合主办的徐光荣《浴血淬火的灵魂》新书首发暨作品研讨会在沈阳举办。在这本书中,徐光荣以《犹记阳光下白朗甜甜的笑容——三见白朗追忆》深情地回忆了白朗。
徐光荣说,短篇小说《只有一条路》是白朗创作生涯的起点,文中14岁少年王加栋“不愿再受欺压”、决心走出困境寻找生路的信念,正是白朗毕生创作的起点——人的觉醒。文中“他望着天边的星星,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走,走出去才有活路”的表述,不仅是少年的呐喊,更是白朗对那个时代的发声。此时她的笔触虽略显生涩,但已能体现出对压迫的敏锐感知与反抗意识。
“这些活动开阔了白朗的视野,也使她懂得了许多革命的道理。所以白朗的创作从一开始思想倾向就非常明确,那就是暴露黑暗、歌颂反抗。这在她的代表作《沦陷前后》里也有深刻体现。”徐光荣介绍,小说《沦陷前后》里,白朗清晰地记录了民族蒙难给她带来的毁灭性记忆:“我记得很清楚,而且,这记忆永远不会从我的脑子里溜走。1931年9月18日。”“故乡,仍在敌人的掌握之中,故乡的同胞,被嗜杀无忌的魔鬼生吞活剥了,开膛破肚,奸淫抢掠了!”
白朗的创作初期,聚焦于民众的觉醒与反封建,后期在抗日烽火中得到锤炼,愈加刚劲。研究东北作家群的徐光荣如此评价——在白朗的创作初期,她充分利用《文艺》为阵地,发表了大量反满抗日的文学作品,直到1934年罗烽因共产党嫌疑被捕,她在组织帮助营救罗烽出狱后,流亡到关内,投奔先到上海的萧军、萧红,成为东北流亡作家群的重要成员,并从此在左翼作家联盟中从事革命文学创作活动。
从“河畔”微光到觉醒之路
“在鲁迅关爱与帮助下,萧军和萧红这时发表了令文坛瞩目的《八月的乡村》与《生死场》,一举成名。白朗也想像萧红那样,在为生活奔波中坚持写作,她决定以罗烽被捕,在狱中坚持斗争以及营救他的曲折历程为题材,写一部暂名《狱外记》的长篇小说。”徐光荣在《浴血淬火的灵魂》一书中写道:因为上海“八一三”淞沪会战后,形势日趋险恶,她和罗烽不得不随抗日救亡的文化大军转移,辗转于武汉、长沙、桂林、贵州等省市,最后到达重庆。一路上,她一直坚持写着《狱外记》,直至后来到达延安时才脱稿,长达32章,其中一、三、四章曾在当时很火的《谷雨》杂志发表,引起抗日救亡文艺战士的关注。
徐光荣认为,罗烽被捕是白朗创作的重要转折,这段经历使她的文字“从呼吁个人解放转向呼唤整个民族的解放”。脱离东北沦陷区的直接压迫后,白朗的创作视野从个体觉醒扩展到民族抗争。流亡至上海期间,白朗的创作更趋成熟。1936年创作的短篇小说集《伊瓦鲁河畔》便是明证。小说中,日本宣讲团到村中大谈“王道”,农民贾某表示不满,却被“勒上嚼子,如同牲口一般”,最终被义勇军解救,一同拆毁浮桥上山反抗。徐光荣评价:“这是东北作家中,较早直接描写义勇军武装斗争的作品,无需口号式的呼喊,反抗的力量却能深入读者内心。‘文中的浮桥拆了,就像把鬼子的锁链砸断了’的语句,至今读来仍令人热血沸腾。”
在《轮下》《生与死》等作品中,白朗将个人命运与民族苦难交织,以细腻笔触揭露侵略者的暴行。徐光荣特别提及《轮下》中“母亲在雪地里数着孩子的脚印,一步一哭,脚印尽头是鬼子的军靴印”的段落:“不直接使用‘残暴’二字,却让读者不寒而栗——这正是她创作的细腻功力。”徐光荣说。
从哈尔滨《文艺》副刊到延安《解放日报》,从反封建的呼号到抗日的战歌,白朗14年的创作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东北民众从苦难到觉醒反抗的精神变迁。徐光荣总结:“她的文字中,既有女性的细腻,更有战士的刚毅,既有文学性又有革命性——这在东北女作家群中独树一帜。”
从北国烽烟到文坛双生花
“白朗与萧红,堪称命运与共的知己,战斗在抗日烽火中的双生花。”鲁迅美术学院影像艺术学院副教授、辽宁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程远征如此形容二人的关系。
“在哈尔滨时,白朗和萧红就是可以常常促膝交谈的闺中好友,她主编的《文艺》副刊,还为萧红编发了《王阿嫂之死》等许多小说。当时萧红、萧军婚后没有固定收入,生活困窘,白朗以招记者之名,为二萧每月发50元工资,两位初登文坛的女作家相依相帮,成为北方革命进步文坛的两朵新葩。”徐光荣介绍。在哈尔滨“星星剧团”的舞台上,二人的情谊进一步加深。徐光荣介绍:“她们共同出演《居住二楼的人》,白朗饰演的律师太太与萧红扮演的老妇人,在舞台上生动展现了阶级压迫的现实。”
1933年,萧红陆续发表《看风筝》《小黑狗》等作品,将东北大地的苍凉与民众的挣扎跃然纸上;白朗则同步创作《叛逆的儿子》等短篇,以尖锐视角刻画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二人的文字相互呼应,共同构成北方文坛的“抗日先声”。
程远征介绍,在许鞍华导演的电影《黄金时代》中,在表现萧红不同阶段的人生故事时,会不时让她的朋友跳出故事情节,对萧红的命运进行口头讲述或者点评,以此串联起萧红短暂动荡的一生,而白朗则是贯穿始终的一位。
银幕上的白朗,与现实中在哈尔滨为萧红“以薪代助”、在重庆为她送去棉衣时同步创作《老夫妻》的白朗,共同勾勒出一段“以文为友、以笔为援”的抗日烽火情谊。1942年萧红病逝于香港后,延安《文学月报》刊发了白朗的《遥祭——纪念知友萧红》一文,编者按语称:“白朗是萧红踏上文学之路的最亲近的女友,又是除萧红之外流亡的唯一东北女作家。”
程远征认为,这份情谊超越了个人范畴,“她们是东北作家群中的两朵金花,14年间以文字为镜、以创作为灯,既映照出彼此的文学初心,更共同照亮了东北作家群‘以笔抗日、以文救国’的前行道路。”
责编:齐志扬
审核:刘立纲
Copyright © 2024 lnd.com.cn 北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