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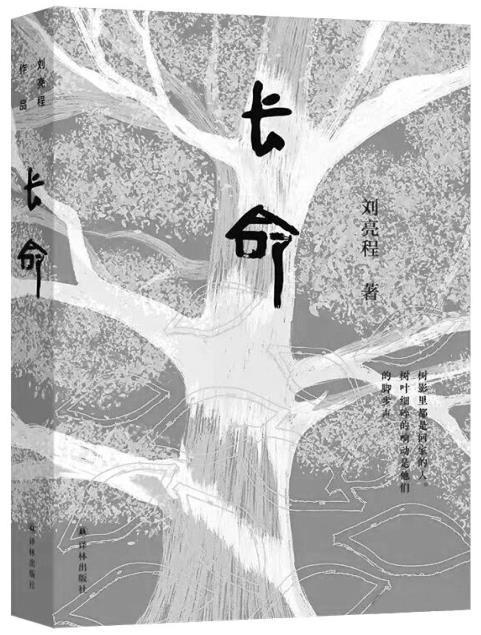
刘逸南
■提示
刘亮程的最新长篇小说《长命》近日出版,这是他继《本巴》荣获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后的首部长篇新作。被作者自称为“天命之作”的这部小说,标志着刘亮程创作生涯的新高峰。《长命》不仅是一个关于村庄的故事,更是对生命本身的长久沉思,是对民族文化根脉的深邃探寻。
通过《长命》这部最新作品,刘亮程完成了从《一个人的村庄》到诠释一个民族的厚土长命的文学飞跃。《长命》的故事起源于新疆戈壁深处的“碗底泉村”,以主人公郭长命与神婆魏姑的双重视角,构筑了一个现实与超现实交织的村庄世界。刘亮程探索了“生命并不是短短百年,而是祖先的千年和子孙的万世,这就叫千秋万代中国人的厚土长命”。
刘亮程的语言风格在《长命》中达到了新的高度。他保持了《一个人的村庄》中的诗意与哲思,又增添了更为深沉的历史质感。他的语言像戈壁滩上的风,粗糙中有细腻,简单中蕴深邃。
小说中充满了典型的刘亮程式意象:钟声、风、尘土、长夜、梦境、魂魄。钟声尤其重要,它是一个核心意象:“钟声一响,草里的虫会醒,水里的鱼会动,土里的亲人会睁开眼睛;树影里都是回家的人,树叶细碎的响动是他们的脚步声”。刘亮程的语言具有一种独特的节奏感,仿佛古老村庄的呼吸,缓慢而深沉。他写死亡:“死是另一层活”;写生命:“我们站在祖先与子孙之间,被时间延续成长命,上下皆是生命前行的路,这是生命永远的路”。这些语句虽简单却饱含哲理,展现了作者对生命本质的深刻洞察。小说采用双线叙事结构,通过魏姑的第一人称自言自语和第三人称叙述交替进行,形成了多声部的复调效果。这种叙事方式既保持了故事的神秘感,又让读者能够从不同角度理解人物和事件。
《长命》最显著的艺术特色是现实与超现实的交融。小说中,人与亡灵共处,生死界限模糊,构建了一个“有天有地、有人有鬼、有生有死”的完整世界。刘亮程打破了现代文学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回归到中国民间传统的世界观中。在那里,生死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生命的两种不同状态。他说:“生意味着区分万物,而死连接万物,唯有在大千世界的死死生生中,才能理解生命。”
刘亮程的创作手法令人想起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但又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他的魔幻不是拉美的魔幻,而是中国乡村土生土长的魔幻,源于中国传统的自然观和生命观。小说通过家谱、祠堂、钟声等意象,强调了文化传承的重要性。刘亮程认为:“你能记住多少辈祖先的名字,你从前的命就有多长”,死去的人命也由后人延续。
《长命》也是对现代性的一种反思。小说中,现代性表现为村庄搬迁、土黄牛改种西门塔尔牛等。这些虽然带来了经济利益,却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传统文化的断裂。刘亮程没有简单地对现代性进行否定,而是通过文学的方式呈现了其中的复杂性。构建了一个“厚重而混沌、温暖而完整,我们曾共同拥有的生活图景”。这部小说帮助我们重新忆认民族的精神原乡。
在文学史上,《长命》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新方向——从对西方现代派的模仿回归到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刘亮程汲取了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营养,创造出了瑰丽的中国文学世界。
“我跟中国所有作家都不一样的是,我有一个地窝子里的童年。”刘亮程坦言。《长命》与刘亮程的个人经历密切相关,融合了他60年的人生体验。他从出生到12岁,一直伴着恐惧长大——夜深人静时虫子打洞、树根钻土的声音,还有地下不远处坟地里的动静,深深植入了他的生命感知。小说中的许多元素都来自刘亮程的生活经历:与作者同年出生的主人公郭长命、行医的父亲、手抄家谱、童年的玛纳斯河。甚至小说中的返乡之路,也是刘亮程在40年后亲身踏上的祭祖之路。刘亮程曾在《一个人的村庄》中吞下了“贫困、恐惧、孤独”,而在《长命》中,那个8岁孩子眼中的惊惧与悲伤又重现了。他坦言:“到了60岁,那些疼痛还在,从未真正消失。”这种个人疼痛与民族记忆的交织,使《长命》具有了特别的情感深度。
《长命》是刘亮程60岁时完成的“天命之书”,它只有在作者到了这个年龄才能写成。正如刘亮程所说:“我的每部小说的题材似乎都有一种宿命感,必然会在某个年龄遇到它。”这部小说像一场等待了十年的雨,终于在天命之年降落在中国文学的土地上。《长命》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的文学成就,更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回到传统文化根脉的可能性。
钟声里,有祖先的智慧,有民族的记忆。《长命》里承载着中国人特有的生命观,也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精神密码。
责编:李莹
审核:刘立纲
Copyright © 2024 lnd.com.cn 北国网